我在白公馆大约待了三年。1953年,西南公安部在松林坡建了一所新的监狱,我们遂搬进了这所正规的监狱中。
松林坡监狱比白公馆大得多,这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里住六个人。每天起居生活,安排学习都井井有条。吃的、住的条件都很不错。这里除了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大小战犯外,也有少数犯了错误被判刑的共产党干部。
有一天,监狱的所长叫把所有关押犯人的房间都打开,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只见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进一个上了大刑的人进来。这个人戴有很重的脚镣、手铐,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地直响。大家一看,都很吃惊:“这人犯了什么罪,上这么重的大刑?”后来听完所长的介绍,才知这人原来是共产党内的一个中级干部,因利用手中的权力到处吃吃喝喝,贪污受贿,犯了错误。此事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每个人都感到共产党真是执法严明,不论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受到处分。从这里大家也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我们这些人确实够宽大的。论罪行,多半都是严重的,但共产党对我们却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还百般地照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这种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通过这几年的改造,联系到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共产党不但在军事上要比国民党有战略眼光,就是在经济建设、治理国家上也比国民党高明得多。从下面几件事,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49年,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致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十分混乱,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几乎被老百姓当作了废纸,一口袋钞票在市场上换不来一个鸡蛋,致使人民怨声载道。当时,我就想过,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搞到这种地步,即使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一副烂摊子也够收拾的。哪怕你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使物价稳定下来,不是三言两语或是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需要有充实的物质力量,而这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是根本没办法办到的。但是,不到一年的工夫,共产党政府竟基本上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物价。当时,我就很奇怪,共产党究竟用了什么方法使物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呢?
为此,我一方面看报纸,一方面向人打听,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民众。过去,由于交通不方便,许多县里的粮食都有剩余,积存在县里运不出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根本无法运出来。共产党一取得政权就立即发动广大的群众,让大家自动地把多余的粮食运到交通方便的地方。这样,用粮食做基础,以此来调节市场,稳定了物价,限制了通货膨胀。这一着棋,不能说不高明。
2.进军西藏
1950年春天,我在白公馆时从报上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部队准备进入西藏,并很快同西藏方面签订了和平协定,解决了西藏问题。看到这一消息,我是很高兴的,认为解放军进驻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决策。因为有些国家对西藏早有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的国家想一口吞掉西藏。当年我在滇缅边界同日军作战时就曾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战后将大理、保山、腾冲、龙陵、芒市、片马、拖角、阿敦子、西昌等地划为一特别区,以建设边疆、控制西藏。为了完成这一设想,我曾派参谋处长冯宗毅到阿敦子一带,又邀请西南联大地理系主任张印堂教授为团长到腾冲以北的片马、拖角一带实地调查,同时,我还命司令部高参袁策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当年,我曾把这一设想写成报告,派人送给蒋介石侍从室贺耀组主任,他觉得我的这一设想很有意思,表示支持。这份报告,蒋介石可能也看过,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缺乏全局的战略眼光,西藏问题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国民党军队打通中印公路之后,在云南有十几个军,却从未有派一支部队进入西藏的打算。如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西藏问题恐怕就会很复杂了。
3.抗美援朝
1950年,中国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我们在白公馆知道此事后,大家也是议论纷纷。在我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强大得很,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表示怀疑。
当时,我曾听人讲,对援不援助朝鲜的问题,毛主席也曾找了很多人谈话,要大家进行讨论,发表意见。据说,有不少人表示不该出兵去援助,认为我们只需准备足够的力量守住鸭绿江就可以了。主要理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同时物价还没有完全稳定,经济建设还未开始,国家的元气也没有恢复,现在派军队去,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毛主席洞察全局,最后还是做出了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
这场战争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个侄子宋承舜和侄女都亲身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据他们讲,美国人的飞机每天二十四小时连续地狂轰滥炸,使人不得片刻的安宁。我的侄子是学交通工程的,是个铁路工程师,他有时几天几夜都不能休息。因为交通一中断,如果不能马上恢复,补给供应不上,几十万的军队吃饭就会很成问题。所以,他们只能抓紧时间,利用敌人飞机轰炸的间隙来恢复交通,以保证公路、铁路两条运输线的畅通。宋承舜回国时,整个人似乎都失去了知觉,经过一年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战争的结果是美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板门店签字时,美国的一位将军李奇微曾说:“美国自有陆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停战协定。”
朝鲜一战,确实打掉了美国不可一世的威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意、日被打垮,英、法的实力也受到削弱,苏联的损失非常大,唯有美国在战争中发了财,壮大了实力。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却打破了这个神话,使美国军队丢了脸,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利用租界、领事裁判权,到处横行霸道,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为所欲为,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由于统治者奴颜婢膝,屈从于外国势力的压力,不敢对外国人采取行动,致使中国人在世界上到处受人歧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才真正抬起头来。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外国人再也不敢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耀武扬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我自己也感到受了很大的鼓舞,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此可以挺直自己的腰板了。
4.修建成渝铁路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我国就曾有过从成都到重庆修建一条铁路的计划,当时的政府曾向国外借款,动工修建,但没有修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同法国人谈判,希望外商投资,帮助修建,最后还是没有修。
解放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1950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于当年6月开始组织人力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有些地区还没有平定,但共产党政府却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我们在重庆一听说共产党已开始修建成渝铁路,就感到十分惊疑,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国民党人员,都不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能修好这条铁路。所以,此后对这件事也就不大关心了。可是,没过多久,1952年7月,我们在白公馆里忽然听到了火车的声音,询问之后,方知当天正在举行成渝铁路的通车典礼。一听此信,我们个个都是既惊又喜。惊的是共产党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修成了前人想修而未修成的铁路,喜的是从此由成都到重庆的交通再也不用发愁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也很大,感到过去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只说空话,不干实事,共产党则是扎扎实实地干了再说。
上述几件事情对我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经过认真的思考、对比,我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讲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的偏见,开始相信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一些政策和方法了。这样,自己的世界观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影响,开始对自己追随蒋介石反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
五、功德林里的改造生活
思想改造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立场、观点,非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不可。政府为了加速对我的改造,决定把我从重庆送到北京学习。因此,我于1954年由重庆松林坡来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
我到功德林后,管理人员安排我单独住一房间,不到几天,心情就觉得烦闷起来。原来在重庆先是三人,后是十来个人住在一起,大家有说有笑,看报、下棋。可现在一人关在一间房里,既没有聊天的对象,也无下棋的对手,最可悲的是连报纸也看不到。这样,我思想上又有了很大的波动。
一天、两天,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盼望能和大家在一起。由此也生出了不少怨言,自觉这几年改造已有了不小的进步,为何反而越改造越糟糕,蹲起小号了呢?不到半年的工夫,我的身体开始感到不适,脑袋经常感到眩晕。有一天,我感到头晕得不得了,医生得知后给我一检查,血压高达二百多,随即将我送进公安部医院诊治,在医院躺了十多天。血压平复后,才又回到功德林。在我的诊断书上,医生写的是“神经性血压高”。显然,这与自己的苦闷、思想波动有关。
我从医院回来后不久,管理所的王科长找我谈话。他叫我看两本揭露四大家族的书,并说:“你认真地看一看,看完后写个总结,谈谈自己的感想。”这类材料,我在重庆时就仔细读过,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篇将近千字的读后感。递上去后,王科长又找我谈话,说:“你的总结写得不错,有一定的认识。这样吧,我看你一人也挺闷的,去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去吧。”就这样,对墙面壁、顾影自怜的苦闷生活终于结束了。
离开小单间,我同邱行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被编为一组,住在一个房间里,又过上了集体生活。
1955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学习,读书看报、讨论时势,以提高思想觉悟。大约到了这年的11月,有一天屋里的人除我和邱行湘外,其他的人都搬走了,同时杨伯涛从别的组搬到了我们住的房间。我们三个谁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知其他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我们才搞清楚,原来是内部调整,以准备安排从外地集中到功德林来的人住。从这时起,我们的伙食大大地改善了。每顿饭由一菜增加到两菜一汤,主食也有所改善。
不到十天,功德林里陆续来了不少人,有一百二十人左右。范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金城等由山东调来,早已来到功德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交谈了。一见这么多老熟人,大家都很高兴,彼此相贺,庆幸余生。
管理所把这一百多人分成十一个组,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我和王耀武负总责,管理这一百多人的学习与生活。但把这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集中到一起到底干什么,我们谁也猜不透。
1956年1月11日上午,功德林的负责人、原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礼堂给我们做了一次重要讲话。姚局长的讲话解除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使我们知道了集中是为加速对我们的改造,以便使我们早日成为新人。接着姚局长还谈到对我们在初期改造中不得不采取强迫改造这一形式的原因,并宣布今后准许家属、亲友前来访问及对外通信。最后,姚局长勉励我们自觉地进行改造,还向我们宣布说,不久将组织大家出去参观,让大家看一看国家发展的情况。
姚局长的话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从这时起,由于大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谈心、交流意见了,所以每个人学习的劲头都有所增高,整个功德林的气氛也比过去活跃多了。
1956年的五六月份,管理所组织我们在北京附近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北京市的市容、北京郊区的水利建设。另外,我们还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工厂,尤其在市郊参观某棉纺厂时,给我的感触最大。
这个棉纺厂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不久的工厂,厂里大多是女工。据厂方领导介绍说,这些职工在旧社会人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她们中有一部分是北京原来八大胡同的妓女,靠卖身维持生计。解放后,政府为安置她们,兴建了工厂,让她们参加劳动。现在多数人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厂里还有一部分人,曾参加过帮会组织,过去专干绑票等不法之事,政府对这部分人在进行劳动改造后,现在也给予自新之路,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5.听完介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旧中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她们中的大多数是良家女子,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旧社会的帮会组织是很多的,青帮、洪帮,四川的袍哥,这些这些地痞、流氓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过去外国冒险家到中国来也是好事没干,坏事做尽,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作奸犯科,用尽各种办法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鸦片之害,尽人皆知。在旧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过去军阀统治时期,他们在云南、四川大种鸦片,将鸦片运往香港、天津、上海等地贩卖,赚到钱后又向外国购买军火,造成了中国长时期的内乱。鸦片对中国人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毒害确实很大。记得过去我有一次到重庆,过江后要上山,叫了一乘滑竿。抬滑竿的轿夫长得面黄肌瘦,上山一趟,沿途竟要抽三次鸦片。山道边设有专卖鸦片的馆子。一间小房,在窗口架了几杆烟枪,烟是早已装好的,交钱后,马上就可以吸。我当时很奇怪,就问他:“你们为什么抽鸦片,难道就不能不吸吗?”轿夫说:“抽上了瘾,不吸烟就没有精神,上不了山。”由此可见,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之深,烟、赌、娼确为中国的三大祸害。所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先是禁种,再是禁卖、禁吸鸦片,从而使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了。能在几年之内,使毒害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烟、赌、娼绝迹,以及扫除过去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在大陆上的真正统一,确实是做到了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祖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不能不说是个壮举。
这年的7月间,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到管理所来看望我们。先后来的人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卫立煌及一些朋友。能同他们谈一谈,听听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分析是很有意义的。据他们中有些人透露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有意在不久要特赦我们,大家知道后都感到很兴奋。当年确实已准备在秋天特赦一批战犯,但又因故推迟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对国内的形势有些影响,所以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1957年5月间,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北去参观,到了沈阳、长春、鞍山,参观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铁西工业区、长春市容等。东北之行,一共三个星期。参观归来,大家都感慨不已。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社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回到功德林后不久,大约在这年的7月间,我们又启程到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和一个现代化的屠宰场。回京后,又继续学习。通过这几次参观,我们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国家在这几年里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在谈心得体会时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争取尽快地得到政府的宽大,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六、获得新生
1958年秋天,管理所组织我们到秦城进行劳动锻炼。但规定年老多病、身体太弱的人不能去,继续留在功德林里学习。因为我有血压高的毛病,身体不大好,所以领导上要我留下,不让参加劳动。但在我一再要求下,领导上经过讨论,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参加劳动的人共分为五个队,身强体壮的编为一、二队,年老体弱、身体差些的编为三、四队。我当时被编入了第三队。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们遂于这年的10月中旬跟着带队的管理干部来到了秦城。
秦城坐落在京郊北面燕山山脉的脚下,附近群山迭起,绿树成荫。山上的龙泉古寺,小汤山的亭台楼阁、涓涓温泉早已久负胜名。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呼吸到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我的精神豁然开朗,自觉一下子又年轻了许多。
开始劳动时,一、二两队到大田里干活,我所在的这一队是上山栽果树和负责果树的管理。刚到秦城时,我的思想还有些负担,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劳动过,怕乍一干起活儿来吃不消。可没想到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活儿,每天只有半天劳动,另外半天学习。过去也常听人讲过,犯人劳动改造就是服苦役,每天累得死去活来。其实,共产党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想惩罚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劳动锻炼,培养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使我们能够树立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目的仍然是为了改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新人。
在秦城劳动时,我们的伙食搞得很好,每天还可以到河边去洗澡、洗衣服。而且劳动时能同大自然相接触,心情很愉快。所以,我认为在我将近十年的改造生活中,这一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精神最愉快的一个时期。
通过劳动改造,我端正了自己的劳动观点,联系到自己的过去,初步认识到自己过去骑在人民头上所过的那种剥削的寄生生活是可耻的,多少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的感情。
1959年10月间,领导叫我们回到功德林继续学习,又叫我们写自己被俘以后,通过学习、劳动的一些思想体会。12月4日这天早上,领导忽然通知大家把衣服穿整齐些到礼堂去开会。待我们整队进入会场时,才知道要开特赦大会。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全部特赦,还是部分特赦。
10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最高人民法院领导讲话后,开始宣布特赦名单。当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一时竟不知所措。我们第一批特赦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和我三人当时曾登台代表被赦人员,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表示感谢,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特赦大会之后,我们回到驻地,马上换上了政府发给我们的新衣服,整顿行装。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长亲自来接我们,他用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市区的旅馆。这样,我们遂告别了功德林,从战犯管理所走上了新社会。
特赦之后,抚今思昔,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我在长沙上中学时读过一篇古文,是欧阳修的《纵囚论》。这篇文章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曾于贞观六年,将三百多名准备处死的囚犯放回家,让他们料理一下后事,与家人再团聚一次。临走时同他们约定好期限,到时叫他们“自归以就死”。等约定的日期刚到,“而卒自归无后者”,竟然全部回来了,于是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们。当时,我读到这一段,觉得唐太宗确是了不起,对他的做法感到十分佩服。可今天仔细一想,唐太宗的做法和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待战争罪犯的做法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唐太宗的纵囚,不过是沽名钓誉,收买人心。正如欧阳修所说:“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我们这些罪犯采取的方法却是既人道又实际的改造方法,目的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人能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要比唐太宗的做法更具有积极性,进步得多。
翘首神州,更觉往事如梦如烟。但这十年的改造生活,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回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把我从一个战争罪犯改造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rekoe,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www.mulub.com/724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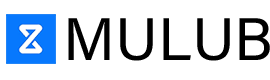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